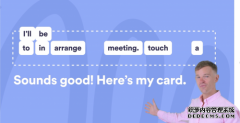现代性背景下的应急情报体系
时代的转变给社会标注了令人炫目的多样性标签,诸如“开放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网络社会”等等,无论哪一个标签都呈现了现代社会新的特征,“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无疑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两个方面。风险社会使应急管理面临更加复杂和多变的场景,对应急情报体系的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信息社会则为情报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和资源条件。《现代性背景下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以社会为中心的构建》一书正是谈及在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双重影响下的应急情报体系的构建问题。
“情报”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东西。1915年版的《辞源》中认为“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是情报。1939年版的《辞海》则定义情报是“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追溯其来源,“情报”一词实由郭沫若等留日学生引进。日本近代文学三大文豪之一的森欧外,于19世纪末留学德国期间翻译了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将军事信息翻译为情报。故而,情报最早用于军事上,其战略定位是“耳目、尖兵和参谋”。随着我国图书情报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出的“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成为情报更为普遍的含义。
应急情报体系,顾名思义是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应急决策服务的情报系统。应急管理的对象是危机事件,危机常常具有形成的突发性、应对的紧迫性、影响的公共性和发展的扩散性。因此应急情报就有别于常态管理机制下的情报,需要响应和服务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这些特点。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应急情报体系都是以分类管理和分层集中为特征的。但是“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整合分散于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的应急响应体系,建立了所谓的“系统之系统”,其中多个子系统与应急情报体系直接或者间接相关。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再次提示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应急情报体系的建设,打破部门、层级和地域的藩篱,构建无边界信息流以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
《现代性背景下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以社会为中心的构建》一书剖析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景象,即风险不仅来源于自然,也来源于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多种来源的风险的交织混合产生了一个以新型风险和不确定性为标识的“失控的世界”。它呈现出三类特征,即风险的全球化、风险环境的改变和风险意识的改变。这些改变对应急管理和应急情报体系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1)风险全球化的挑战。风险的全球化特征体现于风险强度在全球范围的增长和风险环境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核灾难、生态灾难、经济崩溃、网络瘫痪、隐私泄密造成的社会动乱,以及其它潜在的高强度风险引发的危机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性破坏,其影响超越了地域和时间,也超越了贫富差距、知识差距等一切可以划分的社会等级。突发事件不断增加和叠加,使世界上的每个组织和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突发事件及其后果愈发难以预防、控制和管理。
(2)风险环境的挑战。由于自然环境已经或正在被社会化,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和社会变化之中,风险环境进入到“人化环境”阶段。在 “人化环境”中,制度化的行动及其社会场所为新的风险的扩散打造了温床,并随着全球化机制的普及,资源与服务将脱离地域的控制,使制度化风险环境得到极大发展。制度化风险环境使风险的产生和扩散形成制度性依赖,其因素与后果之间相互影响,使应急管理的机制和模式受到挑战。
(3)风险意识的挑战。随着风险景象的改变,风险环境与专业知识的匹配形成了客观上的不对称。一方面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共同危险已经广为人知,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敢于宣称绝对正确地应对突发事件及其后果,这就造成了期望与现实、数据与知识的鸿沟。风险意识不仅发展为一种态度,其本身便成为一种风险。管理者不再能够机械地依靠专家做出决策,而要学习在复杂的风险环境中识别风险和处置风险。
《现代性背景下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以社会为中心的构建》一书从情报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解释了情报体系与应急管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探讨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环境中应急情报研究的范式转变,以及情报体系的资源结构、组织模式、决策支持模式和情报共享机制等问题,有益于启发读者对风险和情报的重新认识。